午时三刻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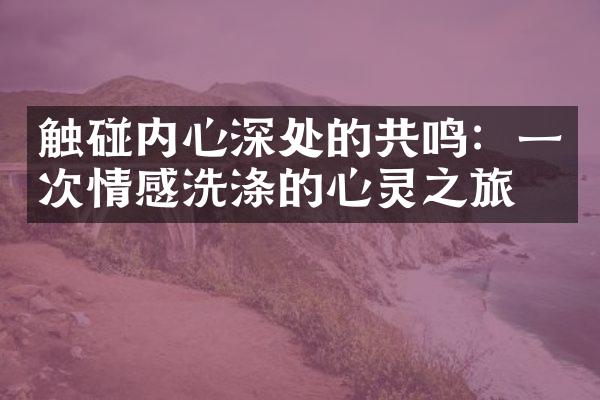
人在梦与醒的境地上踯躅,显出犹豫之态。但脑子总还恍惚着。这恍惚中却有一种东西渗透进来,入梦如入冰窖。
我少年时做了一场大梦,梦见了许多古怪的事物。那些人、那些事,先排成了队,然后又散开,排成各色的队列行进。他们有的胖,有的瘦;有的青面獠牙,有的粉脂如玉。一队里头,总会夹着一两个特别触目的角色,他们也有些像是穿了戏装,只是搭衬得太过,反不自然。看着看着,自己也便夹在队伍中了——瘦削的身躯裹着宽大的衣衫,更加显得支离顶突。
行过的路和景物颇不清,觉着像浙江的老宅,又像是北平的胡同。路面凹凸不平,青石板已经成了暗赭色,有两行破碎的纹路像是用拙劣的刀工刻上去的。墙壁上攀着些牵牛藤,藤叶畸形地扭曲着,与衣服的下摆相混着颤抖。
梦里分明感到某种重荷压顶而来。那重量不像是压在身上,而是径直落入胸腔——左侧第三肋间隙的深处。先是迟缓,感到穿刺的疼痛,既而便是一阵催人欲呕的战栗。这感觉比剃刀的寒光更锐利,又比初冬的湖水更冰冷。有时又忽而轻若游丝,渺茫地浮动在脊背。极细小的气流从每个毛孔里渗出来,浑身便打了个寒噤。
我的左胸处出现了裂口,灰白色的脓液流了一地。那些排队的怪物竟然俯下身去品尝,有的咂嘴,有的皱眉。我想喊叫,却发现自己发不出声来。
噩梦总是逃不掉的,每每此时,我就因为恐慌而睁开眼睛。双眼开合之间,我感觉好似经过了匿形的刽子手的刀口,死了一次又活转过来。摸摸衬衫,已经浸透了冷汗。脸颊像是被什么昆虫叮咬过般刺痛,也许那不过是因为泪水的腐蚀。
醒来之后,倒不如梦中那般痛苦。日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泅进来,照在书桌一隅。那里堆着昨夜未改完的作业,红笔画的圈与叉互相交织,构成了新的迷宫。钟表的秒针跳动着,一圈又一圈地描画着完美的圆。
教师办公室的桌上永远堆着未批改的作业本。A班的张老师鬓角已霜白,五十多岁的人带着三十年前的眼镜,我想他大约忘记了更换。有时听见他咳嗽,咳到弯下腰去,脊椎的轮廓从老式西服里凸显出来,一节一节像是竹竿。他不会知道,在他转身板书时,刘达和王明在底下偷偷地交换了考卷。
我们都是排着队向前行走的人,不知道下一步要迈向哪里。有人的脚步轻快如羽毛,有人的双脚灌了铅;有人是睁着眼前行,有人则蒙上了黑布。每到转弯处,总会有人忽然消失了,人群却毫不在意,继续沉默地前进。警察漠然地站在路口抽着烟,偶尔用警棍轻叩电线杆子,数着消失的人数。他们背着手望天的时候,眼神空洞得像两泓枯井。
中学的操场上总铺着一层黑色颗粒,踩上去吱吱作响。雨天过后,会渗出铁锈的气味。我喜欢站在单杠旁边观看,看同级的学生们奔跑追逐。他们的腿脚是那般有力,以至于踏起了一蓬蓬尘埃。刘青甫的大腿肌肉格外发达,跑起来像一匹小马驹。但在上星期,他被检查出了心脏病,如今只能坐在看台上发呆。他的眼神时常飘向更远的地方,远到超越了校园的围墙,超越了城市的轮廓,甚至可能与彗星的轨道遥相呼应。
我的作业批改到李芳的卷子,她的字迹小而密,像是怕浪费纸张似的。最后一题的空格里写着"我也不明白"五个字,歪歪扭扭的,似乎是匆匆添上去的。我给了她一个丁等,这分数在期末会葬送她的保送资格。笔尖触到纸面时,我忽然看见她站在办公室门口,脸色比纸还白。
窗外的枫叶开始泛红。这红色不像血,倒像是颜料店最廉价的那种赭红,掺杂了过多的褐色。风卷起落叶旋转的那会儿,仿佛有呜咽声传来,转瞬却又消散了。
深夜批改作业时,手指沾了红色墨水的斑点。那颜色逐渐干涸,变成深褐色,像是一块块小小的疤。月光渗进窗户,桌上的台灯就显得黯淡了,笼罩着一圈昏黄的光晕。那天李芳没来上学,往后也永远不会来了。人们在私下议论着什么,而我假装专注于备课。教室里空了一个座位,那空缺的形状刺痛着眼睛。
大雨滂沱的一日,我遇见了刘青甫的父亲。他撑着黑伞站在校门口,伞沿滴落的水珠串成了线。他想告诉我一些关于他儿子的事,嘴唇抖动了许久。我听见雨水打在伞面上的声音越来越响,几乎淹没了他的话语。最后他鞠了一躬,转身走入雨帘中,佝偻的背影竟与他的儿子有几分相似。
枇杷树开花时总是最不起眼的。那些浅黄色的花簇在浓绿叶子底下,轻易就会被忽视。它们散发出隐隐约约的苦香,并不会引来蜂蝶的垂青。直到结出橙黄色的果实,人们才会惊觉它的存在。然后有一天,果实消失了,那树又默默无闻地站在原处,等待来年的花期。
我渐渐学会了不在午夜惊醒。噩梦虽然依旧频繁造访,但我已经能和它和平共处。胸口那个想象中的伤口开始愈合,只留下一道淡淡的痕迹,像是铅笔画的线被橡皮擦去了大分。
某个周末的清晨,我去了郊外的山丘。这里视野开阔,可以望见整座城市匍匐在晨雾中。空气中飘荡着松针和露水的气息,间或听到几声不知名鸟雀的啼叫。太阳升起来了,光线透过云层,描摹出一束束明晰的路径。
山脚下有一所小学校,红砖墙围成的小院子里,几个孩子正在追逐打闹。他们的笑声细碎而尖锐,飘到这里时已经稀释了许多,却还是如同银针般扎入耳膜。城市在远处蠕动着,像是一头睡得不甚安稳的巨兽。无数人在其间行走,他们也排着队,朝着各自模糊不清的方向前进。
下山的路曲折而漫长,我不时停下来喘口气。路旁开着不知名的野花,蓝紫色的花瓣在风中摇曳。它们得如此卑微却又如此倔强,仿佛是对抗荒芜的最后宣言。我想摘下其中一朵,手指刚触到茎秆就缩了回来——那柔弱的生命还是留在原处比较好。
回到城里时已近正午。阳光暴烈地倾泻下来,把街道两旁的悬铃木影子钉在地面上。行人的脚步变得匆忙,他们急着赶往某处,或是逃离某处。我站在斑马线前等绿灯,听见对面商店的收音机里正在播放一首老歌。那旋律莫名熟悉,却又怎么也想不起歌名。
午时三刻的钟声敲响了,在喧嚣的城市上空回荡。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