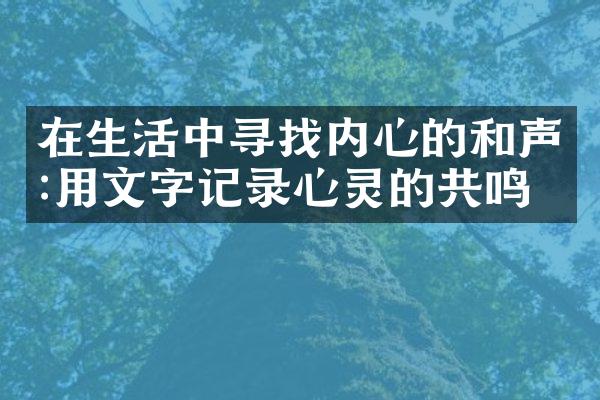如果生命有形状,它应是蜿蜒河流冲刷岩壁时雕出的沟壑,或是种子顶开冻土时伸展的第一片弧度。我们捧着颤动的胸腔探讨存在,不过是为了在时光长河里刻下自己的铭文——以喜怒哀乐为刻刀,以血肉为碑石。

初生的喜是春日裂帛。当婴儿啼哭刺破产房滞重的空气,那声波震颤里迸溅着原始的火星。老作家颤抖的钢笔在稿纸落下墨点,墨汁在纤维中舒展如胎发的茸毛。此刻生命具象成蝴蝶撞破蛹壳时震落的金粉,在阳光下折射出万种可能。
怒焰掠过生命的姿态像灼伤的闪电。少年将拳头砸向教室斑驳的墙壁,石灰簌簌剥落如同褪去的幼稚。中年人深夜掀翻的办公桌上,咖啡渍蔓延成血管的形状。这些暴烈的电弧终会沉淀,在地下岩层熔铸成尊严的矿石。
最深沉的哀伤总是寂静的。老人倚着银杏树数落叶,枯黄的弧形里飘着十二封未寄出的信。医院走廊尽头亮起的红灯在凌晨三点熄灭,有人从此学会用真空保存泪水。死亡不是终点,而是将记忆锻打成琥珀的压强。
而乐是羽毛笔蘸着月光写下的诗行。新婚夫妇在暴雨中相拥奔跑,积水迸溅的音符溅满裙摆。实验室蓝光里炸开的晶体,向宇宙宣告又一道谜题缴械。幸福从不在蜜罐里繁殖,它更偏爱裂缝间挣扎向上的野草。
当酸甜苦辣在血管里完成第两千次循环,我们突然读懂生命的隐喻——它既是梵高笔下旋转的星空,又是显微镜下分裂的细胞。那些澎湃的爱意与尖锐的苦痛从未相斥,恰如春天怀抱残雪绽放,冬夜存着篝火入眠。
于是作家把颤抖的指纹摁在稿纸末端,就像远古人类将掌印拓在洞穴深处。所有的欢笑与泪痕终将风干成历史岩层,而永恒的,是灵魂在虚无中奋力描摹自身轮廓的姿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