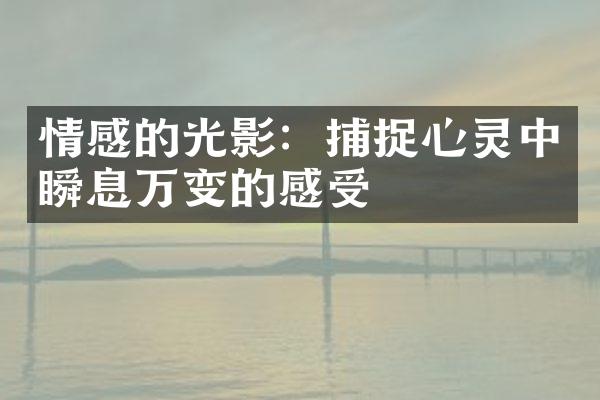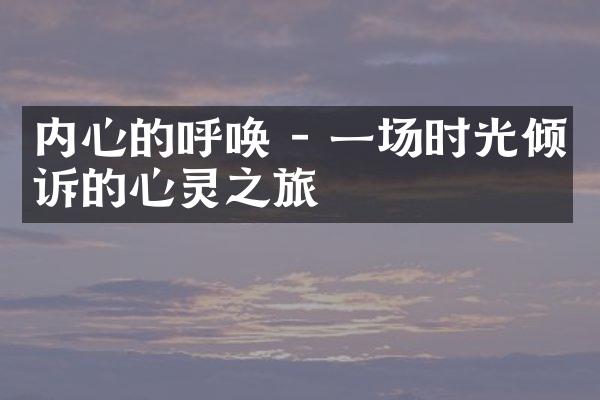日光斜斜地透过纱帘,在旧相册封面投下细密的光斑。指尖抚过烫金标题时,《家春秋》三个字泛起温润的哑光,像祖母常年摩挲的玉镯。掀开扉页的瞬间,樟脑气息裹挟着时光的颗粒扑面而来,那些被岁月压平的棱角,此刻都在记忆深处重新变得立体丰盈。

相纸上的母亲还绾着乌油油的麻花辫,在筒子楼公共厨房翻炒辣子鸡。炒锅腾起的白烟里,她脊背弯成的弧度恰似雨后青竹,将五岁孩童的整个世界安稳地拢在油盐酱醋的奏鸣曲中。蒜瓣爆香的噼啪声穿透三十年光阴,至今仍在耳蜗里轻轻震颤。那年冬季她拆了旧毛衣给我改制手套,织针在煤油灯下拉出绵长的金线,我说指尖新萌的冻疮痒得钻心,她便放下活计捧着我的双手呵气,薄荷膏的清冽混着白兰花头油的气息,在鼻腔里结成永不消散的暖流琥珀。
父亲的老式二八自行车后座藏着整个宇宙。放学路上经过食品厂,他变魔术般从工装裤兜摸出烤得焦脆的边角料饼干,我啃着锯齿状的甜蜜,将脸贴在他汗湿的棉布衬衫上,数着脊背凸起的脊椎骨如数一串神秘密码。有次暴雨突至,他脱下工装罩住我头顶,自己却淋得透湿,深夜透过阁楼地板缝隙,听见他用浓重的川音给母亲念我幼稚的作文,当读到“爸爸比杨树还高”时,低沉的笑声震得吊灯铁链叮当作响。
祖母的陶土药罐在蜂窝煤炉上咕嘟了半个世纪。每到惊蛰前后,她总要从樟木箱底取出绣着并蒂莲的绸布包,将晒干的车前草与枇杷叶仔细称量。药香弥散成雾气的时刻,藤椅上的老人会轻声哼唱早已失传的童谣,苍老的手指在我后背穴位游走如抚过古籍上的活字。她去世那年留下的最后一锅秋梨膏,如今还封存在青瓷坛里,每当舀出半匙冲水,那些随水汽升腾的记忆蜂群便裹着甘甜将我层层环绕。
老挂钟的铜摆依然在客摇晃,只是再也等不到晚归的脚步声叩响门环。我在家族相册的空白页夹进新的合影——婚礼上父母鬓角的霜色映着胸前的红花,满月宴里祖孙三代的指节在镜头下叠成岁月的年轮。当女儿用稚嫩的笔迹在照片背面写下“全家福”时,突然懂得亲人相伴的日子原是时光长河里的萤石,即便被水流推向远方,仍在记忆深处恒久散发着温柔的磷光。
合上相册的刹那,窗外的梧桐正抖落满身夕照。那些琐碎的生活切片经过岁月窖藏,早已在血脉中酿成陈年的酒浆。或许所谓亲情,就是无数微光时刻编织的隐形绳网,让我们在风雨飘摇时始终拥有坠落的安全感——因为无论走出多远,总有些温暖坐标永远固守在时空的某个经纬度,如同家乡屋顶上不曾熄灭的灯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