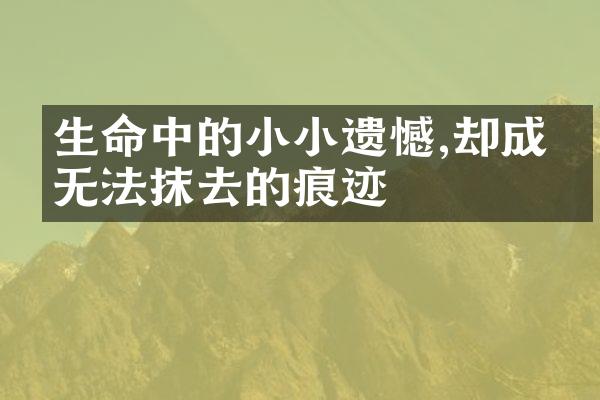雨水沿着老槐树虬结的枝干向下爬行,在树皮交错的沟壑间积成无数微小湖泊。我蹲在滴水檐下看蚂蚁衔着卵粒向高处迁徙,屋檐铁皮被雨凿出的凹陷处,盛着二十年前父亲用止血钳夹出来的半口牙齿。

那个溃脓的夏天始终蛰伏在流年碎片最锋利的裂口里。消毒水浸泡的黄昏,诊室白炽灯管在父亲口腔投下十字形阴影。我数着金属器械碰撞的声响,看他咽喉深处随呼吸翕动的峡谷——血污形成的溪流正蜿蜒漫过悬雍垂,与蛀牙根长期溃烂的堤岸汇合。
母亲在病历背面写满借贷金额的数字如同咒文。旧风扇转动的间隙里,我听见她脊椎在三十七度高温中迸出细密的皲裂声。父亲的被窗外的蝉鸣碾碎重组,最终变成收废品货车播放的电子音乐,永远卡在《兰花草》第四小节的降调处。
十年后拆迁队推倒诊所的早晨,我在废墟堆里拾到半枚牙冠。树脂补料的裂缝中嵌着1999年的光斑,像枚来自时间琥珀的信物。挖掘机履带碾过的地方,土层向上翻卷出解剖学横切面般的肌理,露出地下蚯蚓啃噬出的暗河——那些交错的孔道如同疼痛的化身,在地下构建着永不见光的根系王国。
母亲如今仍会半夜摩挲着拆除钢钉的左腿骨缝入睡。阴雨天不锈钢床架传导的微电流,让她枯萎的坐骨神经末梢重新模拟出年轻时的幻痛。“身体像本沙之书”,她撕着关节上的死皮说,“每次翻开都会掉落新的伤痕页码”。
上个月暴雨冲垮了后山的黄土坡,塌陷处裸露出层层叠叠的鞋底印。考古队推测这是明清流民躲避战乱的藏身堑壕,我却认出私奔那晚踩塌的泥径。她红色塑料凉鞋细跟捅穿的泥层下,露着半截被树根吸收殆尽的童尸遗骸——这方土地向来擅长将苦楚腌渍成无机物,再随季风撒向每个屋檐下的晒场。
暮色四合时,我站在新形成的雨水冲沟边缘向下眺望。雨季塑造的地质伤痕正吞吐着五百米深度的黑暗,沙土层在夕照里呈现出沉疴淤积的绛紫色。沟底传来塑料棚残骸被水流扯碎的声响,如无数个相似夜晚里母亲捶打风湿关节的钝击,回荡在时间纵深处早已钙化的苦痛矿床。
淤青色的云块从西北方碾来之际,第一滴雨精准落在我左眼旧伤的缝合线上。这个被摘除晶状体的器官,终于学会从降水中析取记忆封存的盐分。当千万道雨线开始雕刻大地新的沟回时,整座山谷都在持续溃烂的伤口里,分泌出珍珠质包裹的固态光阴。